网络上有食物史爱好者节选过《剑桥世界食物史》的中译短文。但是,整部著作的中译本直到现在尚未面世。由于该书属于“剑桥中国史”系列,其品牌影响力、学术权威性,学术界、业界十分认可。倘若有眼光和实力的出版社可以拿下该书版权,并与我方合作翻译,该项目可以落地。故而,在此发布潜在合作项目信息,有意者可以与我方联系。 邮箱:hongcheng@mail.zjgsu.edu.cn
手机:+86-13732217263
背景资料:转自网络文章:《剑桥世界食物史》绪论 翻译:山寨盲流 校对:Ent From: Kenneth F. Kiple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Fo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0.
还在阅读《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1993年出版)的校样时,我们已经着手开展“剑桥食物与营养的历史与文化”课题。就在那时,我们开始考虑把对人类健康历史的研究扩展到食物与营养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需要关注的绝不仅是对健康的损伤。编写疾病史时我们尚可以参考August Hirsch在他的三卷本《地理历史病理学手册》(London,1883–1886)中提供的范式。而本书却没有什么“地理历史食物与营养手册”可供借鉴,因而本书也可算是独辟蹊径了。
幸而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不缺乏;我们有200位左右的作者和编委,代表了从农艺学到动物学的数十门学科;这使得本书与前作《剑桥疾病史》一样,代表了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协作努力,其目标是扼要概括我们所知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以来的食物与营养的全部历史。我们希望在这二十世纪将近尾声之际,这部两卷本的营养学图书能够与《剑桥疾病史》一同,就人类健康的全部已知和未知的知识,为现在和未来的学者提供一个剪影。
本书的主题中,有两点已经在书名中体现出来。食物,自然是书中所写历史的核心;没有食物就没有生命和历史,因此我们使用相当多的篇幅来叙述全球最重要的食物的历史。从某种角度说,这可以看成是数量方面的描述,而与之相对的是,营养——人体对食物的需求以及处理利用的方式——对于塑造人类生活质量则至关重要。因而我们也在本书的纵向结构中列出了一系列营养学课题,阐述其对于过去与现在的人类的重要性,以图为我们未来的营养状况提供建议。
尽管书名并不包括“文化”一词,但这个字眼出现在本课题名称中,而且文化的概念的确渗透在书中,自我们狩猎-采集远祖的史前文化始,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形色色的饮食文化,直至现代的“食品政策”,其制定与实施的动力常常是源自文化规范。最后是“健康”,尽管从来没有在书中的标题中出现,却或明或暗地包含在每一章节中,同时也是本书的根本出发点。
概述
我们希望第八篇(译注:第八篇:世界食用植物词典 Part VIII A Dictionary of the World’s Plant Foods)中,定义了书中涉及的植物食品并概述其历史的那些词条,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重要工具,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别感兴趣于那些地理区域相关章节感兴趣的读者而言;因此我们认为在本节的概述中首先涉及这最后的部分更有操作性。此外,由于水果基本上在食谱中只扮演季节性的配角,因而除了极少的几种作为主食者之外,水果都归到第八篇中。对于土豆(也有专门章节叙述)或芦笋这些食品,大多数读者不需要特别解释,但是诸如西非荔枝果(ackee)或泽米属(zamia)(在加勒比海地区相关章节中涉及)之类较罕见或者地域限制性的食物,读者可能想要多了解一些。一方面,第八篇记录了这些罕见食物,使得作者无需在行文中对其做出枝节性的解释说明,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上佳的机会,以便集中精力探究食物的起源与应用。另外,第八篇也是本书中记录同义词的部分,读者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如果他们原先并不知晓的话)aubergine是茄子,”swede”是一种芜菁甘蓝,”Bulgar”则来自bulghur,意为 “碾碎的谷粒”。
第一篇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起始,第一篇的各章节构成了对于早期人类,以及现今的狩猎——采集人群所消耗食物的一次体质人类学上的考察。无论从哪一个进化阶段开始算,人类都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但是发明出农业和驯养牲畜则只是过去1万年左右的事,只占到人类在地球上存续历史的微小的百分之一而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人类必然是我们远古祖先从食腐者到熟练猎人,从食物采集者到种植者的演化之旅中所经历的饮食进化的产物。
探究我们狩猎-采集祖先的食谱(所消耗食物的内容)以及营养状况(人体处理食物的情况),可供采用的手段林林总总。考古遗址贡献动植物遗骸,还有人类粪化石(干燥粪便),能够解释食谱问题,而人类遗骸——骨骼,牙齿,以及(偶尔的)软组织——的分析则帮助阐明营养问题。此外,研究现代的狩猎-采集人群的食谱和营养(饮食考现学,周鸿承注),也为判读前述的考古资料提供了帮助。到目前为止,可以总结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旧石器时代祖先吃得不错,而且比后来的定居者还要相对优越一些。实际上有一些专家主张这些狩猎采集者吃得比他们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之前的所有后代都好。
第二篇
第二篇把焦点由觅食转向耕作和动植物的驯化。食谱由猎取和采集来的食物向生产出的食物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然而由于其开始时间与许多大型猎物消失的时间吻合,这就引人猜测,可能是当时食物逐渐匮乏造成的迫切需求才促成了农业的诞生。不过无论定居农业如何出现,随之而来的营养退化基本上都要归咎于所谓超级粮食的出现——大米、玉米、木薯和小麦——这类主食供养了大量人口,却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主要是因为食谱过于集中在此类主食上,无法获得对于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的广谱维生素、矿物质和全蛋白。
第二篇中的章节编成若干组,多数是讨论我们最重要的植物食物,归类在数个标题之下,从“谷物”、“根,块茎,及其它高淀粉主食”,到“重要的蔬菜”,以及用于榨油和调味的植物。所有这些论及植物的章节都讨论其最初驯化发生的地点,方式和驯化者,以及随之而来的向全球传播,还有其现在的地理分布。论及驯化,自然就要谈到植物与人类的互相依赖关系,即所谓“互利共生”现象,连同现代的种植问题及技术,都在文中得到一些详细研讨。
植物食品的移植造成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冲击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然而这一影响——尽管常常是破坏性的——对人类历史至关重要。小麦,一种约一万两千年以前随着冰川的消退而开始繁盛的草本植物,大约两千年后在中东首次得到(明显)有意的种植。到公元前一世纪,仅仅为了供养罗马城中人口,每年就需要一千四百万蒲式耳 小麦,这导致了一整套扩张行动,最终使罗马人把北非大部分的可耕地变成了麦田。因此,尽管相传是马可•波罗(1254?—1324?)从中国带回来面条的概念,显然意大利人在此之前很早就拥有面食了。(从植物发展史角度回答历史学问题,周鸿承注)然而只有等到富含维生素C的美洲番茄传入之后,意大利人才能烹制出意粉与番茄酱的绝配——面食从此不仅更加美味,而且更加健康。而在中国,来自新世界的番茄与玉米、土豆、番薯和花生,各自通过不同途径进入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其结果则是引起了人口的剧增。
换言之,移植美洲植物的意义并非像用番茄配意粉这样,仅仅是丰富了旧世界的餐桌。玉米,木薯,两种甘薯,花生和辣椒被奴隶贩子用船带到非洲西海岸,本意是用来喂饱他们的黑奴“货物”。而这些新食物不仅喂养了前往美洲的奴隶,也喂养了他们的后代,它们的成功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美洲作物在非洲触发了农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粮食供应的数量和质量,也带来了人口暴涨,填补了奴隶掠夺留下的缺口,而被掳走的黑奴则在美洲种植蔗糖和咖啡(当然还有其它作物)——这两者都移栽自旧世界。
欧洲接受土豆和玉米的速度要慢得多,不过其影响还是一样显著的。旧世界小麦每次种植只能收获五倍于播种量的产出,而玉米能收获25到100倍(现代玉米一穗能收到约1000粒),到十七世纪中叶,玉米成为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农民的主食,在法国南部则稍次要一些。从那里开始,玉米开始传播到整个欧洲,而到十八世纪末,玉米粥(在意大利叫做polenta)已经经由奥斯曼帝国传到巴尔干和俄罗斯南部。
同时,数个世纪来的城市的发展以及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尤其是香料贸易——加速了探索全世界的食物并使之全球化的进程。对油料的探索也同步展开(用于烹饪,食物储存以及药用),这个进程开始于椰子被冲上热带海岸时,橄榄树沿着地中海由黎凡特传播到伊比利亚大西洋海岸时,以及芝麻成为北非和亚洲大部勃兴之中的文明的一部分时。
十七世纪的侵略,饥荒和驱逐迫使爱尔兰农民选择土豆作为最少耕地产出最大的作物,在十八世纪,由于其它作物常常歉收,土豆得以传入德国和法国。从那里开始,这种作物向乌拉尔山脉传播,那里原来只有黑麦,只能在短暂而且常常多雨的夏季成熟。土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势良好,而且每英亩能够提供相当于黑麦四倍之多的卡路里,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土豆已成为北欧一大部分居民活命的口粮,正如玉米对于南边一些地方的人口来说也是不可或缺。
玉米还能间接养育人类。确实,有了玉米作为饲料,现在更有可能让牲畜越冬,以获得全年稳定的肉类供应,加上以奶、奶酪和蛋的形式提供的全蛋白——过去只是少数人的享受,如今多数人都能得到。于是,有人认为欧洲人口从十八世纪初开始增长,并于十九世纪达到一个临界点,开始以数百万的规模向外殖民,这绝不是巧合,欧洲人迁徙的方向与早前被抓走的黑奴去向相同,正是那些创造了粮食剩余的植物的故乡。(再次表现出植物在世界范围内的移植在人口统计学上的意义)
第二篇最后一组章节论述动物源的食物,讨论范围从野味、野牛、鱼类直到家畜。这不多的几章解释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对植物界的依赖。实际上,世界上的植物性食物还协助驯服了上述的动物——就像最早驯服的狗一样——它们使得动物甘愿被驯服,这对人类食谱的贡献的重要性无法估量。
狗似乎是首先被驯化的动物,也是唯一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被驯化的。它的祖先狼曾是食肉者和捕猎者(与人类一样),在发展历程中的某个时刻,似乎人类与狗结成了联盟,虽然有时人类会把狗当作盘中餐,有时又会反过来。而可以确定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冰川开始退缩,气候变得温和,草食动物开始繁盛,日益增多的绵羊和山羊发现人类种植的谷物(或者至少是人类看守着,等待收获的野生植物种籽)是最容易找到的饲料。这些新农民无疑很快就不再赶跑它们,而是捕捉——最初是作为配合谷类食品的肉源,也许稍晚就开始尝试利用绵羊的绒毛和山羊的防水羊毛。
捕捉动物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使用在需要献祭的宗教仪式之中。事实上,有一种主张认为野生水牛、牛、骆驼,甚至山羊和绵羊最初都是出于献祭的目的来捕捉的,而不是为了吃。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对于可驯化动物来说,捕捉之后的下一步就是畜牧了。在东南欧和近东(这种早期活动大量发生的地点),野生山羊和绵羊可能是最早体验到生活方式巨变的——它们清除地面上所有可食用物质的天赋得到它们新主人的发掘和充分利用。很快就出现了放牧的羊,牧人与他们的羊群广泛地散播出去,向更多的人介绍了驯化动物的奥秘和价值。
野猪则并非反刍动物,因而也就不太容易受到地里庄稼的诱惑,这意味着它们不会主动接近人,于是人类只好主动去接近它们。野猪很久以前就被猎取作为祭品,而且很可能给狩猎者留下性格暴烈的深刻印象。公元前7000至6000年之间,人类农场开始驯养猪,这一历程肯定是困难重重。
野牛无疑是被吸引到人类的农田里来的,不过根据我们目前对已灭绝的欧洲野牛(现代牛的野生祖先)的认识,公元前6000年左右对牛的驯化恐怕比驯化猪需要更多的勇气。然而这份辛苦绝对值得,因为不仅可以得到肉,奶和皮革,牛还可以与绵羊山羊一起为农业生产出力——把种子踏入土中,脱粒,拉车,以及(稍后的)拉犁。
现代最重要的驯养动物中,最晚驯化的的是鸡,首先用作祭品,然后则用来斗鸡,人类最后才开始食用鸡和鸡蛋。这种丛林鸟类的驯化品种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中国北方;但是由于现代鸡种是东南亚和印度两种野禽的后代,因而最初的驯化地点仍然无法确定。野鸡被人类种植的谷物吸引而来,然后被捕捉,鸽子也是如此(直到不久前为止,鸽子在人类食谱中的重要性都一直比鸡还高)。鸭,鹅等等野禽都很可能是被新石器时代新出现的农业产品所吸引——并被捕获的。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水生动物以及骆驼,牦牛,还有美洲驼和羊驼,纷纷为智人Homo sapiens所驾驭,这一“智慧人种”不仅攀上了食物链的顶端,而且还下决心要延长它。
第三篇
第三篇讨论了人类最重要的饮料,从古至今它们总与人类的主食形影不离。其中的水本身就是生命的要素;另一种,人类母乳则——至少到不久以前为止——是新生儿存活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物种延续的必要条件。而这两者同时也是人类疾病的传染源,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狩猎-采集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基本上不足以弄脏泉水,水塘,河流或者湖泊。但是定居的农业族群却会造成污染,而且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排泄物,还有他们养的动物。人类定居点在哪里兴起(其中有些地方就成了后来的城市核心),水媒传染病就在哪里滋长,水——生命的要素——也就转而威胁生命。饮料的发明于是就显得既令人愉悦又充满智慧,因为发酵的过程能够杀菌。确实,人类最早的文字记录就提及用大麦、粟、大米以及其他谷物酿制的淡色浓啤酒(ale),还有椰枣和无花果调制的棕榈酒——这都说明早自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期开始,酿酒就已经是一桩重要的买卖了。
公元前3000年前后,葡萄酒展露头角,蜂蜜的产地也出现了蜂蜜酒。蒸馏酒精制造威士忌和白兰地的方法在七、八百年前被发现,到中世纪末(约600年前),人们在淡色浓啤酒中加入啤酒花(“hopped”),酿出了真正的啤酒。看起来古人为了防御水媒传染病所投入的智慧和心血实在是蔚为壮观。
奶作为动物驯化的额外收获,也被人尝试发酵,尽管结果并不总是很理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酸奶、奶酪和黄油的生产终于变得稀松平常,甚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乳糖不耐者,都能够接受这些乳糖含量较低的乳制食品。只要当地有出产,奶(尤其是牛奶)就是断奶儿童的食物,而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奶也被用作婴儿的母乳替代品,尽管有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难题是牛奶的营养物质过于浓缩,而且人体会形成针对牛奶蛋白质的抗体,因此牛奶远非完美食物,尤其不适合婴儿。另一个问题是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与普通结核共同肆虐欧洲的牛结核病(淋巴结核)。奶妈是喂养婴儿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充满危险,而在约瑟夫•利斯特和路易•巴斯德之前,人们毫无消毒意识的年代里,人工喂养造成的婴儿死亡数字大得惊人。
将水煮沸是又一种预防水中病原体的手段,而且与发酵一样,这个过程也能产生美好的饮料。中国人从汉朝时期就开始饮茶,到了唐朝(618—907),饮茶大行其道,从此以后,中国人对茶的热爱就再也没有减退。中亚游牧人也接受了这种饮料,后来将其带到俄罗斯。饮茶在六世纪左右传到日本,不过直到约700年后才开始流行。这种调制饮料再从日本传到印度尼西亚,很久以后(1610年左右),荷兰人在那里发现了茶,并将其带回欧洲。几十年之后,英国人主导了这种饮料的普及推广,而他们最终把持了茶的贸易则更是人尽皆知。
尽管咖啡传入欧洲的时间与茶相近,它的历史却要近得多,所谓的咖啡传奇始于九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到1500年,咖啡已经遍及阿拉伯世界(那里是禁酒的),再过几个世纪,这种饮料在欧洲也相当流行了。传说中欧洲人与咖啡的初遇机会,是在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放弃对维也纳的围城时,遗留了几包咖啡豆。
来自美洲的可可,加入到亚洲与非洲对世界饮料的贡献之中。由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有了可可的生长地,他们成了最早享用巧克力(在哥伦布之前的中美洲人中间早已流行很久了)的欧洲人。在十六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巧克力饮料传过整个西班牙帝国,到达意大利和荷兰,在该世纪中叶又传到英国和法国。
于是,在依靠酒精来对付不清洁的饮用水一千年之后,人类终于有机会利用这三种几乎同时传入欧洲的饮料来保持相对的清醒(当然期间还需要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风行过程”)。不过还需要加入糖这一重要成分使它们变甜,才利于人们接受。而这些饮料的日益流行,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奴隶贸易的加速,美洲种植园的兴盛,以及法国于1763把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以换取盛产蔗糖的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
不过,蔗糖种植与处理,又给日益增长的酒类名单中加上一条——朗姆酒,然后在十九世纪,糖又成为新兴的软饮料工业的基石。咖啡因是这些混合物中常有的成分,可能部分因为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咖啡和茶提供的提神作用。美国最早的可口可乐制造商在兴奋性上面走得更远,他们加入了古柯coca——来自一种南美洲安第斯山民嚼食的含可卡因的叶子。古柯很快从配方中撤掉,只是饮料名字还叫Coca-Cola,不过可乐果cola还在。正如南美人嚼食古柯叶一样,西非人嚼食可乐果肉也是由于其兴奋作用,不过这回是咖啡因的作用。而且可乐果仁提取物不仅富含咖啡因,而且含有一种心脏刺激物,这一套混合物是碳酸饮料行业中的重要成分。
东非人嚼食一种叫做阿拉伯茶的常绿灌木叶子,同样也用它做成一种类似茶的饮料。最后还有在太平洋地区广泛饮用的卡瓦酒kava,这是世界上最不为人所知也最受争议和最神秘的一种——因为其所谓的麻醉效用而受争议,又因为其仪式功能和文化重要性而显得神秘。
除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发明和饮用的种种饮料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早先,特殊功能的水可能来自泉眼或者某种其它水体,或许是被认为具有魔力,或者是味道甘美,或者就是觉得干净安全。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富人都到有矿泉处旅游,在那里让自己的身体从内部和外部同时“喝水”,矿泉水同时也因为号称的保健功能被装瓶出售(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如今,尽管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家庭都有供水(或者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对功能水的爱好并无减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瓶装水代替了原来是用于替代水的酒类。
第四篇
第四篇关注主要营养物质的发现历史及其重要性,营养物质摄入不足引起的营养缺乏症,现代人的食谱与主要慢性病之间的关系,以及食物相关的失调症。而吊诡的是,许多此类通常危害较大的疾病(尤其是营养缺乏症),只有在发展了定居农业的人群中才会流行。
由于在新石器时代若干次农业革命中,涌现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食物,因此至少到不久前为止,定居农业一直都被视作人类的一大进步。但是生物人类学家的发现(将在第一篇中讨论)表明,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倾向于以目的论的眼光看待历史,才产生出这种论断;而进步实际上也带来了自己的代价(确实,只需要随便瞥一眼报纸,你就能体会到,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需要警惕技术进步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前文曾提及,农业和定居生活造成食谱集中于单一的作物,如旧大陆的小麦和新大陆的玉米,而尽管定居本身能促进人口增长(与狩猎采集生活正相反),但是这种增长却是一种造成营养状况降低的“强行”增长。
后续的进步不可避免地带来更多的营养障碍。促进伊比利亚人把帝国疆域扩展到大洋彼岸的导航与造船技术,同时也造成他们的海员在船上完全不能摄入维生素C,于是坏血病开始在水手之中肆虐。当玉米开始在欧洲,非洲和美国南部扎根的时候,新的食用者还不懂得在食用之前用石灰处理——美洲原住民可能是经过长期实践才学会的办法。而在缺乏经验的人群中,尤其是缺少其它饮食补充的人群中,欠缺烟酸的玉米主食广泛引起糙皮病的4D症状:皮炎(dermatitis),腹泻(diarrhea),痴呆(dementia)以及死亡(death)。十九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机械碾米高效地剥离了米粒上富含硫胺(维生素B1)的麸皮,在食用大米的人群中广泛地导致硫胺缺乏引起的脚气病(译者按:beriberi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不是脚癣)。
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里,维生素的发现使得人们可以通过食物“添加”来终结传统的营养缺乏症,至少在发达国家可以做到,不过那里这类疾病已经在减少。但是其它的健康威胁却迅速取而代之。从20世纪50年代起,癌症和心脏疾病的发病率高涨,最大的嫌疑犯是环境恶化,而食物添加剂就名列其中,包括味精(谷氨酸一钠MSG),甜蜜素(环己基氨基磺酸),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还有糖精。同样受怀疑的还有“工程改良”庄稼,原本是为了防虫害——同时也有可能使其更加致癌——以及定时播撒到农田里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它们通过庄稼作物和饮用水进入人体。
家畜现在则富含抗生素和存在阻塞动脉危险的脂肪,还有促进这种脂肪生长的激素和类固醇。鸡蛋被发现充满了如今听来已经很吓人的胆固醇,而全脂牛奶和大多数奶酪中的脂肪则让寻求“有益心脏”食谱的人士直犯嘀咕。盐被怪罪为高血压的病因,糖则被牵连到心脏病,饱和脂肪被看作是癌症和心脏病的罪魁,缺钙则是骨质疏松的源头。难怪在人均寿命越来越长的发达国家,许多人反而忽然极度关切自己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然而讽刺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若有机会分享这种丰裕的话,是不会在乎这些危害的。对于面临感染危害的婴幼儿而言(母亲们甚至只能用不清洁的水调制配方奶),肥胖、厌食和慢性病都可能是可以容忍的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刚断奶的幼儿遭到蛋白质和能量摄入不足的侵害;没有实施食物添加的地方,碘缺乏(以及其他矿物质和维生素缺乏)影响着数以亿计的儿童和成人;还有营养不足和饥荒。上述种种,到处都是司空见惯。
营养失调可能是我们远祖的狩猎—采集生涯遗留下来的遗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要避免其危害,比发达国家人民更困难。糖尿病(可能是一个影响碳水化合物代谢的“节俭”基因造成的)就是其中之一,高血压也有可能;还有一系列隐藏在各种食物过敏,敏感性与不耐症中的疾病,最近才刚刚得到应有的关注。
第五篇
第五篇各章节以轻松的笔调概括了世界各地的饮食历史与文化,从远古时代近东和北非的农业起源写起,继之以亚洲发生早期动植物驯化活动的地区。随后的章节讨论欧洲,美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大洋洲。
第五篇B章用五节篇幅叙述南亚,中东,东南亚以及东亚的饮食历史。其中一节把中东和南亚合并在一起,是因为伊斯兰美食对于后者强大的影响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阿拉伯人到达之前的几千年里,希腊,波斯,雅利安和中亚地区对南亚就没有影响。
更不能说南亚地区自己没有历史悠久的传统饮食。毕竟世界上许多食用植物源自印度河谷,并且世界上大多数水果和调料也起源于亚洲广袤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一地区也是我们的“超级食物”之一——大米的故乡,大米联系起了这片大陆南部各地的饭食,而小米和(后来的)小麦则是北方的主食。亚洲还是两种改变人类历史的植物的故乡。来自东南亚的甘蔗,日后曾给非洲,欧洲和南北美洲带来苦难;来自东亚的一种常绿灌木的叶子,后来被炒制成茶叶。
稻米早至7000年前就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种植。至今在那里还能找到其野生品种。不过稻米耕作技术很有可能是从中国长江三角洲传播到韩国,然后在约2500年前传到日本。大豆和茶也是从中国传到这些亚洲的边远国家,这些渊源在中国南方、日本和韩国的食谱中留下了一些共性。而中国北方则贡献了面条,所有这些地方饮食,在甘薯、马铃薯、辣椒和花生等美洲植物到来之后,得到了大大的丰富——美洲的植物最初是由葡萄牙海船在十六世纪(到达中国)到十八世纪(到达日本)之间带来的。
缺乏作为钙源的乳制品也是东亚食谱的一个特征。有趣的是中亚游牧民(他们在数千年中,不是在骚扰中国北方,就是在统治那里)食用乳品;他们甚至用母马的奶酿造出一种叫作马奶酒kumiss的饮料。可是乳品没有在中国流行起来,也就没有传播到东亚其它地方。然而在印度,另一批游牧者——亚利安牧民——在4000年前左右传入了乳制品。乳制品在那里倒是流行起来了,不过通常是以乳糖不耐者可以接受的形式——这一症状在亚洲人口中普遍存在。
看到C章(欧洲)和D章(美洲)较大的篇幅,读者可能会指责说这就是一本声称着眼全球的著作中,明显存在西方偏见的例证。但是实际上是因为西方的食物与饮食习惯比其他地方的得到过更多系统性研究,于是这一领域也就拥有更多专业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章中负责各地区的作者都是由史前时代开始,带领读者了解各个特定地理区域的新石器(农业)革命,并关注随后由气候和文化交流所引起的饮食文化的变迁,此外还介绍了新的食物。后者最初是从中东和近东流入欧洲的蔬菜水果,以及一场早期的香料贸易,把各种亚洲、非洲与近东特产带到地中海的西缘。而罗马帝国的扩张则将上述的食物与香料传遍欧洲。
不用说,对于1492年之后,在旧世界各国与新世界各地区之间所发生的动植物交流,本书描述得相当详细,因为这些交流深刻地影响了所有这些地方的食物(以及人口)历史。当然了,在欧洲人来到之前,美洲人已经在他们自己历时数千年的新石器革命中驯化和传播了玉米、木薯、红薯、土豆、花生、西红柿、辣椒以及一系列豆类,并以之维生。不过这样的美洲食谱中缺乏动物蛋白质。仅有的一点动物蛋白来源于猎物、豚鼠、水产、昆虫、狗和火鸡,因地理位置而异。美洲印第安人为什么不驯化更多动物——以及为什么不从他们驯化的动物(例如美洲驼)身上挤奶——仍然算是个谜。比较没有悬念的是美洲土著人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一场欧洲人无意中利用疾病发动的大屠杀。而这片新领地上的人口减少了之后,又布满了马、牛、羊、猪等等来自旧大陆的牲畜。
新世界的植物食品配上旧世界的动物食品,自是金玉良缘,而当负责各个地域的作者行笔至当代——实际上是写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严格地说,是二战以后)时——一个重要的主题从字里行间浮现,那就是在食物全球化的强大力量面前,独特的地方风味渐渐消逝。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烹饪风格,正在同质化,甚至是太平洋,北极和亚北极地区的原住民,也越来越多地食用西方式的加工食品,不幸的是这对他们有害无益。
E章用三节篇幅记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太平洋岛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饮食文化,就此完成了一场环球美食之旅。尽管乍看上去这三地历史上毫无瓜葛,从营养学角度来看也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实际上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比较缺乏可食用的动植物物种。
在非洲,这种缺乏主要应归咎于降雨量,在不同地域,总是过少或者过多。前者酿成灾荒,后者则带来淋溶作用,造成土壤中氮和钙的流失,因而当地的作物也就缺乏重要营养物质。此外,40英寸以上的降雨有利于采采蝇的繁衍扩张,这种昆虫所携带的致命锥虫造成非洲许多地方无法蓄养牲畜。即使能养活,用作饲料的植物也缺少营养,造成牲畜个体大小以及产肉产奶的质量都不如世界其他地方。与南北美洲的情况类似,定居农业时代到来后,多数非洲人的日常饮食并不以动物蛋白为主。
可是非洲不像南北美洲那样,在植物食品方面那么得天独厚。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小米、薯蓣以及一种非洲大米,聊以养活本地人口,在一种比较高产的薯蓣品种横渡印度洋而来之后,人口进一步增加了。但是只有等到奴隶贸易带来的玉米、花生、甘薯、美洲薯蓣、木薯和辣椒传入,非洲人口才开始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飞速增长。
大约三万至四万年前,太平洋先民开始从东南亚一波波扩散,占据了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诸群岛。他们过着一种渔猎采集的生活,食用各种鱼类,鸟类以及爬行动物,还有蕨类的根和其他野生蔬菜。但是一批较晚的移民,在约六千年前从东南亚渡海迁移到太平洋岛屿上时准备更充分,他们带上了猪、狗、鸡以及薯蓣和芋头之类块根作物,这都是旧世界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成果。而很久以后,一种美洲作物——甘薯——以某种方式传遍了大部分岛屿。
所以说,太平洋岛屿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实际上是“进口”来的。不用说这个传播进程会很慢,但是到了库克船长驶入太平洋的时候,所有有人类定居的岛屿也都拥有了猪、狗和家禽——甚至包括最与世隔绝的夏威夷群岛。然而,当欧洲人送来动植物新品种的时候,太平洋岛屿原住民与美洲原住民一样无福享用。他们很快就染上输入的致命疾病,人口骤减。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情况与非洲和太平洋岛屿截然不同,最初与欧洲人接触时,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新西兰毛利人都还是狩猎采集者(后者不完全是)。他们既没有猪和家禽,也不种薯蓣和芋头,只有一种中等身材的狗,还有甘薯。
新西兰在人类到来之前是没有陆生哺乳动物的,不过有巨大的不会飞的鸟类和大量爬行动物。毛利人自波利尼西亚出发前往新西兰时,波利尼西亚已经有了猪和芋头,可是他们在某个时点(或许是在前往新西兰的路上,或许是到达之后)失去了猪,而且新西兰的土壤和气候不利于芋头的生长。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相似,他们也保留了狗,有时也把狗当作食物,甘薯是他们最重要的作物。
于是,除了养狗和一些种植的努力外,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毛利人非常倚重狩猎采集活动,直到欧洲人带来新的动植物物种。不幸的是,正如在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其他地方一样,他们还带来了新的病原体,结果自然还是人口锐减。
在环球游历之后,第五篇以一章对烹饪历史的讨论作为结尾,这一领域目前在欧美蓬勃发展,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必将会有全世界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讨论。
第六篇
第六篇专注于食物与营养相关的课题,涵盖了当代与历史上各个时期。其中有人类以惊人的适应力应对各种特殊营养条件的实例,包括因纽特人的奇异食谱,他们高脂肪的传统饮食足以堵塞动脉,却平安无事地一直生存到如今,令研究者大惑不解。其他章节继续讨论各种特殊时代、经济体和族群的营养需求(以及权利)问题。它们显示了这些需求如何频繁地因文化和经济条件所限而难以满足,并指出母婴营养不足的后果,诸如智力退化等,正在得到详细的研究。在同一主题下,我们也讨论了食物偏见与禁忌;这类行为多数会给妇女儿童带来严重的营养问题,况且生育基本上就是一项营养工作,而长大成人更是一场营养的长征。
对于饥荒的政治、经济和生物原因及影响的讨论,引出了另一个大问题,第六篇的前两章就针对于此。自从Thomas McKeown在1976年出版《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之后,营养在人口历史中的重要性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在这本书中McKeown试图解释:至迟在十八世纪时,英国人——同理可以外推到欧洲人——是怎样成功地跳出人口的“先增长再停滞”这一怪圈的。在排除了医药及卫生的进步,以及疾病弱化或突变等流行病学因素之后,他认为营养改善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用说,如此武断地排除其他选项自然会激起争议,我们还会在其余章节中讨论到一些相反的主张。
与本篇内容相关的还有身高和营养条件的讨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的一个指标。显然,无论营养改善是不是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它都必然在人体发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绝非偶然地帮助了(至少是居住在西方的)人类身高恢复到了他们新石器时代远祖曾达到过的高度。此外,不管人们对于营养和人口之间的关系持何态度,至少都能达成共识——营养与疾病脱不了干系;而我们正有一章专门讨论两者的相互作用。
接下来的章节关注食物的文化和心理学属性,研究人们取舍不同食物的原因,以及与这种食物好恶密切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时下,食物取舍常常成为时尚主题,所以有一章专门讨论造成某种食物忽然流行,又往往迅速失宠的许多原因。
本书用观点截然不同的两章体现了素食主义的争议性——这个话题永远能招来辩论火力。有人把素食归入食疗领域;有人则相信素食的壮阳功能——认为回避动物食品可以促进性欲和机能;有许多人出于宗教信念而吃素;又有些人就是觉得杀生吃肉不对,还有人认为食肉根本就是危险行为。显然,“吃啥长啥”这句话各人都有各自的理解。
第六篇最后几章描述了人类及人类社会是如何以各种方式利用食物或者食物的组合,来操控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与幸福。比如有些食品就被人当作催情剂或者情欲抑制剂大胆地服用,以调节情欲。还有就是一些食品——主要是植物——被作为药用,其中有许多——比如大蒜——会被看成是万应良药。
第七篇
第七篇主要内容是详细探究了食物相关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在从现在到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不过第一章先以营养与国家的关系为起始,揭示欧洲国家如何逐渐地把人口营养条件与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联系起来。接下来的论题有:在确定个人每日主要营养成分最佳摄取量时,所遭遇的无数方法论问题(生物学问题就更不用说了);食物标签的实施问题,如果做到公开公正,则有助于个人作出正确选择以满足营养需要;以及对于非食品补充饮食的效果的质疑。
不出人们的意料,食品安全,食品生物技术以及相关政治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密切关注,而且自然而然的,政治与安全总是步调不一致。这对冤家并非新近结成的,其中一方背后有垄断竞争的资本力量,另一方则代表公众利益。两者并不总是背道而驰,但我们即将看到,二者的关系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首先是安全问题,由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引起。因为所有的作物都是自野生品种演化而来,这意味着,用达尔文主义的说法就是,野生品种在漫长的时间里获得了生存所需的适应能力。然而在驯化与种植中,发生了遗传侵蚀,这种适应力也遭受损失,甚至其野生祖先也可能灭绝;于是今天的很多作物一旦突然间无人种植,直接就会消亡。尽管这种可能性并不怎么吓人——毕竟不可能所有人同时停止种植小麦、大米或者玉米——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了很多遗传特质,我们所种植的这些作物的遗传多样性非常贫乏,并已引发了相当的重视;因为一旦出现某种突变的植物瘟疫,打击了世界粮食供应的相当部分的话,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还有一个问题与遗传多样性的缺损有关。这个问题的潜在威胁相对不那么严重,不过人们并不能因而高枕无忧,尤其是长期的危险性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许多作物已经不太能抵御传统的寄生虫(部分原因是培育过程降低了植物自身产生毒素以防御天敌的能力),因而越来越依赖农药,为农药侵入我们的食物和饮水大开方便之门。
基因工程则号称能够反其道而行,唤醒作物的抵抗力以降低化学污染的危害——例如,把食肉植物与土豆进行杂交,这样落在上面的昆虫就会立刻死掉。可是这种对于植物防御机制的激励也引来了忧虑,因为人吃植物,所以对植物而言人类也是天敌,抵抗力基因有可能使作物不利于甚至是有害于人体健康,如果一旦达到致癌的程度(如前文所述)则更是令人无法接受。同时,基因工程自然更引起这样的恐惧,担心科学家无意中(或故意)制造并释放出自发繁殖的微生物到生物圈中造成瘟疫或生态灾难。
显然,生物科技,植物育种,植物分子和细胞生物学以及农药产业都是前景与风险并存,本书关于食物中毒物的一章就描述了其中一部分风险。而且作为补充说明,关于替代食品的下一章显示,尽管这些代用品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糖和脂肪的统治,但它们自身也并非完美。同样,有一些食物添加剂也不安全。而诸如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之类的防腐剂,味精之类的增味剂,以及柠檬黄之类的着色剂即使多数都是安全的,也仍然使许多人忧心忡忡。
但是,我们的作者明确指出,与科学技术带来的好处相比,其危险性还不如所谓的自然食物中带有的自卫性质的毒素,后者更值得人们操心。例如芹菜含有补骨脂素(原文作psoralin,wikipedia作Psoralen或Psoralene,是诱变致癌物质);菠菜含有草酸,会干扰人体对钙的吸收,并引发肾结石;利马豆含有氰化物;而发绿的土豆皮中含有的茄碱是一种有毒的生物碱。
接下来我们从生物和化学问题转到与政治经济关系更密切的课题上来,诸如生产哪些食物,产量多少,质量要求如何,以及如何分配。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地方),这些政策是由游说团体协商决定的,而他们只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不能代表公众。不过好在即使美国人有时在了解自己吃到的食物上面会遇到障碍,但至少他们还有的吃。美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一种大致的(哪怕有点不太情愿的)共识:获得食物是一项基本人权,而政府应该设法通过补贴、食物券等手段来保证这项权利。 但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就还做不到,那里无钱无势的人常常得不到救济。而本书关于食物补贴与干预一章的作者明确指出,太多的妇女儿童属于无钱无势的人群。
最后,与本书的开端相呼应,第七篇讨论了新石器时代形成的营养模式对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重要性,这个与我们息息相关又引人入胜的问题,也为本书留下一个较为轻松的结尾。
我们以夹杂着乐观与悲观的复杂感情结束这篇绪论。我们给现代作物品种加入矮杆基因,培育出非常高产的小麦和大米品种,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推广,终于促成了所谓“绿色革命”,人们原本希望这能消灭饥荒并帮助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现粮食富余。然而绿色革命同时也在其影响到的国家中触发了一场巨大的人口爆炸,造成马尔萨斯所说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的发展极同时出现。
更有甚者,庄稼新品种极度依赖于石化工业生产的化肥,于是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油价暴涨时,化肥价格随之上涨,造成原先依靠土地收成勉强糊口的穷苦农民破产而失去土地,背井离乡。而新培育的矮杆和半矮杆水稻和小麦携带着相同的基因,意味着全世界大部分的粮食供应在新出现或新变异的植物病原体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更糟糕的是,这些作物似乎连抵抗现有病原体的能力也不足。应对之道似乎只有更加大肆施用农药(环保人士则强烈反对),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承受不起高涨的成本而被逐出农业;而饥荒还在年年肆虐,夺去万千生命。实际上,每一个原指望依靠绿色革命达到粮食富足的国家,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都再次沦为粮食进口国。
显然,无论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角度看,生态不但没有得到维护,反而被严重破坏了。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关于水稻和小麦的章节中所指出的,育种者已经得到携带有能使作物不受流行病伤害的突变基因的新品种,而以培育出不依赖化肥和农药的品种为目标的基因工程努力也有所进展。
同时,本书其他的作者也指出,如果人类集中在大米和小麦上的精力能够分配一些给诸如苋菜,甘薯,木薯和芋头之类的食品,则可以大大扩展世界粮食供应。在这个课题中,我们再次遭遇食物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属性与生态和生物学属性孰轻孰重的难题。这些问题无疑将会影响到人类对高营养新作物的接受程度。
正当一场第二次绿色革命应运而生之时,观察家希望我们能够从第一次革命中吸取教训。不过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看作是第一次绿色革命,研究自那时以来的所有教训——概括起来就是迄今为止的每一次重大的农业突破,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总是使卷入其中的人健康更差,而总体的农业进步则造成人口增长,给生物圈带来严重压力。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我们的希望仍然在于,要能真正从人类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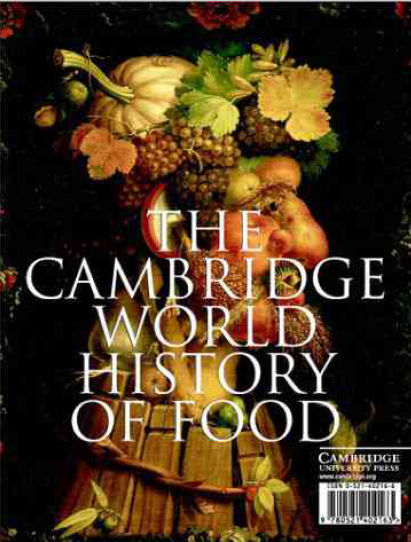
《剑桥世界食物史》目录
第一卷
表格、图片及地图页目录 xix
撰稿人名单 xxix
序 xxxvii
致谢 xxxix
引言 1
第一篇 确定我们祖先的食谱 11
I.1. 先民的食谱重建与营养评估:生物人类学纪录 13 Clark Spencer Larsen
I.2. 营养不良的古病理学证据 34 Donald J. Ortner and Gretchen Theobald
I.3. 根据粪化石所做的食谱重建 44 Kristin D. Sobolik
I.4. 古代的食用动物:根据考古发掘所得的动物遗骸 51 Elizabeth S. Wing
I.5. 食谱重现的化学方法 58 Ted A. Rathbun
I.6. 历史,饮食,与狩猎——采集者 63 Mark Nathan Cohen
第二篇 主要食物:农作物与牲畜
II.A. 谷物 75
II.A.1. 苋菜 75 Mary Karasch
II.A.2. 大麦 81 Joy McCorriston
II.A.3. 荞麦 90 G. Mazza
II.A.4. 玉米 97 Ellen Messer
II.A.5. 小米 112 J. M. J. de Wet
II.A.6. 燕麦 121 David M. Peterson and J. Paul Murphy
II.A.7. 大米 132 Te-Tzu Chang(张德慈)
II.A.8. 黑麦 149 Hansjorg Kuster
II.A.9. 高粱 152 J. M. J. de Wet
II.A.10. 小麦 158 Joy McCorriston
II.B. 根,块茎,及其它高淀粉主食
II.B.1. 香蕉与芭蕉 175 Will C. McClatchey
II.B.2. 木薯 181 Mary Karasch
II.B.3. 马铃薯(白) 187 Ellen Messer
II.B.4. 西米 201 H. Micheal Tarver and Allan W. Austin
II.B.5. 甘薯和山药 207 Patricia J. O’Brien
II.B.6. 芋艿 218 Nancy J. Pollock
II.C. 重要的蔬菜
II.C.1. 水藻 231 Sheldon Aaronson
II.C.2. 葱属植物(洋葱,大蒜,韭菜,香葱和葱) 249 Julia Peterson
II.C.3. 豆,豌豆和扁豆 271 Lawrence Kaplan
II.C.4. 辣椒 281 Jean Andrews
II.C.5. 十字花科植物与绿叶蔬菜 288 Robert C. Field
II.C.6. 黄瓜,甜瓜与西瓜 298 David Maynard and Donald N. Maynard
II.C.7. 真菌类 313 Sheldon Aaronson
II.C.8. 南瓜属 335 Deena S. Decker-Walters and Terrence W. Walters
II.C.9. 西红柿 351 Janet Long
II.D. 主要坚果
II.D.1. 栗子 359 Antoinette Fauve-Chamoux
II.D.2. 花生 364 Johanna T. Dwyer and Ritu Sandhu
II.E. 动物油,水生动物油,及植物油
II.E.1. 油脂概述,重点描述橄榄油 375 Sean Francis O’Keefe
II.E.2. 椰子油 388 Hugh C. Harries
II.E.3. 棕榈油 397 K. G. Berger and S. M. Martin
II.E.4. 芝麻油 411 Dorothea Bedigian
II.E.5. 大豆油 442 Thomas Sorosiak
II.E.6. 葵花籽油 427 Charles B. Heiser, Jr.
II.F. 滋味的贸易
II.F.1. 香料与调料 431 Hansjorg Küster
II.F.2. 糖 437 J. H. Galloway
II.G. 重要的动物性食物
II.G.1. 美洲野牛 450 J. Allen Barksdale
II.G.2. 水生动物 456 Colin E. Nash
II.G.3. 骆驼 467 Elizabeth A. Stephens
II.G.4. 北美驯鹿和驯鹿 480 David R. Yesner
II.G.5. 牛 489 Daniel W. Gade
II.G.6. 鸡 496 Roger Blench and Kevin C. MacDonald
II.G.7. 鸡蛋 499 William J. Stadelman
II.G.8. 狗 508 Stanley J. Olsen
II.G.9. 鸭 517 Rosemary Luff
II.G.10. 野味 524 Stephen Beckerman
II.G.11. 鹅 529 Kevin C. MacDonald and Roger Blench
II.G.12. 山羊 531 Daniel W. Gade
II.G.13. 猪 536 Daniel W. Gade
II.G.14. 马 542 Daniel W. Gade
II.G.15. 昆虫 546 Darna L. Dufour and Joy B. Sander
II.G.16. 骆马和羊驼 555 Daniel W. Gade
II.G.17. 疣鼻栖鸭 559 Daniel W. Gade
II.G.18. 鸽 561 Richard F. Johnston
II.G.19. 兔 565 Peter R. Cheeke
II.G.20. 海龟和海龟蛋 567 James J. Parsons
II.G.21. 绵羊 574 Daniel W. Gade
II.G.22. 火鸡 578 Stanley J. Olsen
II.G.23. 水牛 583 Robert Hoffpauir
II.G.24. 牦牛 607 Richard P. Palmieri
第三篇 饮料
III.1. 啤酒与浓啤酒 619 Phillip A. Cantrell II
III.2. 母乳与人工婴儿食品 626 Antoinette Fauve-Chamoux
III.3. 可可 635 Murdo J. MacLeod
III.4. 咖啡 641 Steven C. Topik
III.5. 蒸馏饮料 653 James Comer
III.6. 卡瓦酒 664 Nancy J. Pollock
III.7. 阿拉伯茶 671 Clarke Brooke
III.8. 可乐果 684 Edmund Abaka
III.9. 奶与奶制品 692 Keith Vernon
III.10. 软饮料 702 Colin Emmins
III.11. 茶 712 John H. Weisburger and James Comer
III.12. 水 720 Christopher Hamlin
III.13. 葡萄酒 730 James L. Newman
第四篇 营养物质——缺乏症,过量症,以及饮食相关的紊乱症
IV.A. 维生素
IV.A.1. 维生素A 741 George Wolf
IV.A.2. 维生素B族:硫胺(维生素B1),核黄素,烟碱酸,泛酸(维生素B3),吡哆醇(维生素B6),钴胺素(维生素B12),叶酸(维生素B) 750 Daphne A. Roe
IV.A.3. 维生素C 754 R. E. Hughes
IV.A.4. 维生素D 763 Glenville Jones
IV.A.5. 维生素E 769 Glenville Jones
IV.A.6. 维生素K与维生素K依赖蛋白质 774 Myrtle Thierry-Palmer
IV.B. 矿物质
IV.B.1. 钙 785 Herta Spencer
IV.B.2. 碘与碘缺乏症 797 Basil S. Hetzel
IV.B.3. 铁 811 Susan Kent and Patricia Stuart-Macadam
IV.B.4. 镁 824 Theodore D. Mountokalakis
IV.B.5. 磷 834 John J. B. Anderson
IV.B.6. 钾 843 David S. Newman
IV.B.7. 钠与高血压 848 Thomas W. Wilson and Clarence E. Grim
IV.B.8. 其它微量元素 856 Forrest H. Nielsen
IV.B.9. 锌 868 Ananda S. Prasad
IV.C. 蛋白质,脂肪,及必需脂肪酸
IV.C.1. 必需脂肪酸 876 Jacqueline L. Dupont
IV.C.2. 蛋白质 882 Kenneth J. Carpenter
IV.C.3. 能量与蛋白质代谢 888 Peter L. Pellett
IV.D. 营养缺乏症
IV.D.1. 脚气病 914 Frederick L. Dunn
IV.D.2. 铁缺乏与慢性病性贫血 919 Susan Kent
IV.D.3. 克山病 939 Yiming Xia
IV.D.4. 骨质疏松症 947 Robert P. Heaney
IV.D.5. 糙皮病 960 Daphne A. Roe and Stephen V. Beck
IV.D.6. 异食癖 967 Margaret J. Weinberger
IV.D.7. 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977 J. D. L. Hansen
IV.D.8. 坏血病 988 R. E. Hughes
IV.E. 饮食相关紊乱症
IV.E.1. 厌食症 1001 Heather Munro Prescott
IV.E.2. 乳糜泻 1008 Donald D. Kasarda
IV.E.3. 食物过敏 1022 Susan L. Hefle
IV.E.4. 食物传染 1031 Sujatha Panikker
IV.E.5. 食物敏感:过敏症与不耐受症 1048 Judy Perkin
IV.E.6. 乳糖不耐受症 1057 K. David Patterson
IV.E.7. 肥胖 1062 Leslie Sue Lieberman
IV.F. 饮食与慢性病
IV.F.1. 糖尿病 1078 Leslie Sue Lieberman
IV.F.2. 营养与癌症 1086 Robert Kroes and J. H. Weisburger
IV.F.3. 营养与心脏疾病 1097 Melissa H. Olken and Joel D. Howell
IV.F.4. 心血管系统,冠心病与钙:一种假说 1109 Stephen Seely
第二卷
第五篇 世界各地的饮食
V.A. 农业的起源:远古近东与北非 1123 Naomi F. Miller and Wilma Wetterstrom
V.B. 亚洲的饮食历史与文化
V.B.1. 中东与南亚 1140 Delphine Roger
V.B.2. 东南亚 1151 Christine S. Wilson
V.B.3. 中国 1165 Francoise Sabban (translated by Elborg Forster)
V.B.4. 日本 1175 Naomichi Ishige
V.B.5. 韩国 1183 Lois N. Magner
V.C. 欧洲的饮食历史与文化
V.C.1. 地中海(饮食与疾病预防) 1193 Marion Nestle
V.C.2. 南欧 1203 Kenneth Albala
V.C.3. 法国 1210 Eva Barl?sius
V.C.4. 不列颠群岛 1217 Colin Spencer
V.C.5. 北欧——德国及周围地区 1226 Hansjorg Küster
V.C.6. 低地国家 1232 Anneke H. van Otterloo
V.C.7. 俄罗斯 1240 K. David Patterson
V.D. 美洲的饮食历史与文化
V.D.1. 墨西哥与中美洲高原地区 1248 John C. Super and Luis Alberto Vargas
V.D.2. 南美 1254 Daniel W. Gade
V.D.3. 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南美北部与中美洲低地地区:早期历史 1260 William F. Keegan
V.D.4. 1492年至今的加勒比海地区 1278 Jeffrey M. Pilcher
V.D.5. 1492年之前的北美温带与北极地区 1288 Elizabeth J. Reitz
V.D.6. 1492年至今的北美洲 1304 James Comer
V.D.7. 北极与亚北极地区 1323 Linda J. Reed
V.E. 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大洋洲的饮食历史与文化
V.E.1. 撒哈拉以南非洲 1330 James L. Newman
V.E.2.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1339 Brian Murton
V.E.3. 太平洋群岛 1351 Nancy Davis Lewis
V.F. 烹饪史 1367 Ellen Messer, Barbara Haber, Joyce Toomre, and Barbara Wheaton
第六篇 历史,营养与健康
VI.1. 营养与死亡率的下降 1381 John M. Kim
VI.2. 营养与死亡率的下降:另一种视角 1389 William Muraskin
VI.3. 传染病与营养:协同交互作用 1397 Nevin S. Scrimshaw
VI.4. 饥荒 1411 Brian Murton
VI.5. 身高与营养 1427 Bernard Harris
VI.6. 发展中世界的妇女营养 1439 Eileen Kennedy and Lawrence Haddad
VI.7. 婴幼儿营养 1444 Sara A. Quandt
VI.8. 青少年营养与生育率 1453 Heather Munro Prescott
VI.9. 营养与智力发育 1457 Donald T. Simeon and Sally M. Grantham-McGregor
VI.10. 人类的营养适应性:生物学与文化的考察 1466 H. H. Draper
VI.11. 食物心理学与食物选择 1476 Paul Rozin
VI.12. 食物潮流 1486 Jeffrey M. Pilcher
VI.13. 食物偏见与禁忌 1495 Louis E. Grivetti
VI.14. 食物的社会与文化功能 1513 Carole M. Counihan
VI.15. 作为催欲剂和制欲剂的食物? 1523 Thomas G. Benedek
VI.16. 作为药物的食物 1534 J. Worth Estes
VI.17. 素食主义 1553 James C. Whorton
VI.18. 素食主义:另一种观点 1564 H. Leon Abrams, Jr.
第七篇 当代食物政策问题
VII.1. 国家,健康与营养 1577 Carol F. Helstosky
VII.2. 食物权利 1585 William H. Whitaker
VII.3. 食物补助与干预婴幼儿营养 1593 Penelope Nestel
VII.4. 建议饮食量与饮食指导 1606 Alfred E. Harper
VII.5. 食物标签 1621 Eliza M. Mojduszka
VII.6. 食物游说与美国饮食指导政策 1628 Marion Nestle
VII.7. 食物的生物技术:政治与政策导向 1643 Marion Nestle
VII.8. 食物安全与生物技术 1662 Michael W. Pariza
VII.9. 食品添加剂 1667 K. T. H. Farrer
VII.10. 替代性食物及配料 1677 Beatrice Trum Hunter
VII.11. 作为膳食补充的非食物 1685 R. E. Hughes
VII.12. 食物毒素与微生物毒素 1694 Gordon L. Klein and Wayne R. Snodgrass
VII.13. 旧石器式饮食与现代健康的问题:推古及今 1704 Kenneth F. Kiple
第八篇 世界食用植物词典 1711
参考资料索引 1887
拉丁名索引 1890
人名索引 1901
主题索引 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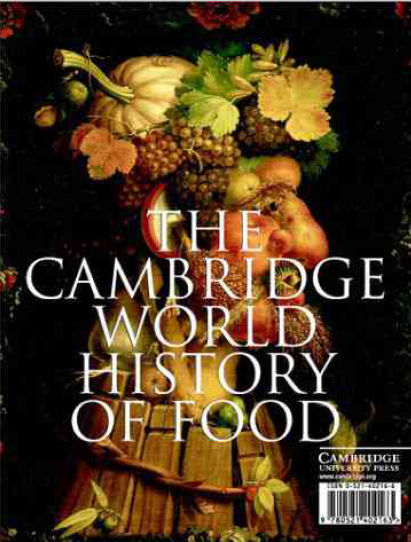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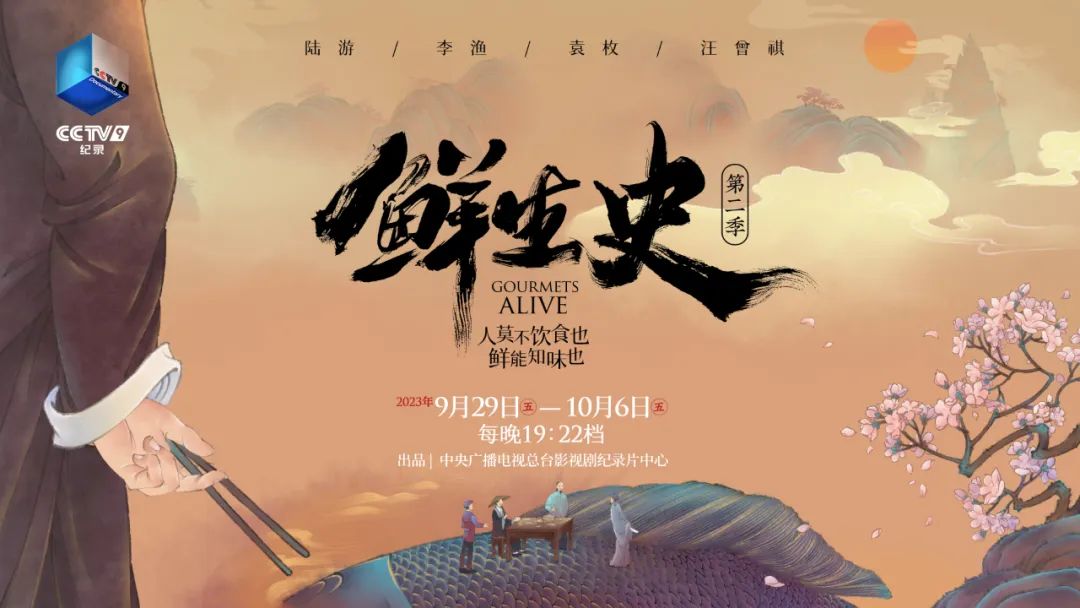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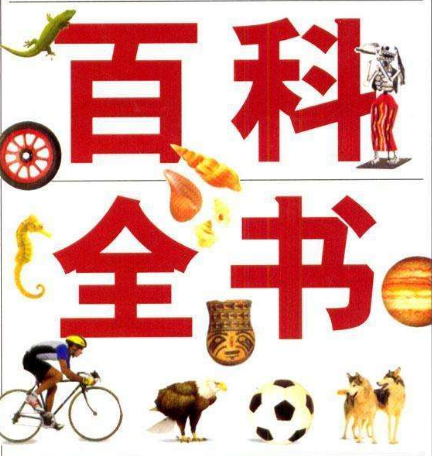
共有条评论 网友评论